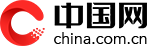李婷玉在學校宣傳推廣古籍修復。

黎彥君修復古籍。

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創始人彭德泉。

李婷玉向小學生演示古籍修復。

彭德泉(右)。 本版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黎彥君。
在成都市龍泉驛區洛帶古鎮,踏著青石板路,穿過各式錯落的客家民居,一棟三層高的小樓映入眼簾:白墻灰瓦、古樸雅致,木門匾上“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幾個字蒼勁有力。
在這里,上萬冊瀕危的古籍經過修復師們“搶救”后,重新被“喚醒”,展現它真實的原貌。四川是古籍大省,全省有200多萬冊館藏古籍,據保守估計,需修復的就占了半數以上。而全省從事紙質修復的工作者有60人左右,修復1冊書至少需要15至20天,“搶救”古籍是個要緊活,但修復古籍卻需慢功夫。
成立于2008年的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從最初的5個人發展到如今40多個人,現已修復古籍1.7萬余冊,是目前全國最大的文獻修復機構。
近日,記者走入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探訪古籍修復師的故事。
三代古籍修復師秉承初心不斷前行,照亮了那些年久失修的典籍,也感動了很多人
修復古籍需要20多道傳統工序,專家大多年歲已高,對古籍修復技藝需要搶救性傳承
越來越多的“跨界”人才,通過走進校園等方式,推廣古籍、活化古籍
“40后”創始人
一生與書有緣,不僅愛書更要護書
人物檔案
彭德泉:中國古籍保護協會理事、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創始人,他一生都在與書打交道,先是讀書,然后在劇團“唱書”,還在學校教書,再到巴中市圖書館管書,最后投身于修書。
一身中山裝、濃眉大眼、清瘦干練……記者眼前這位精神矍鑠的老先生,是已經76歲的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創始人——彭德泉。
一輩子與書打交道的他,對文獻古籍有著滿腔“俠義”之情。他坐在木桌前,一杯清茶,幾卷古籍,向記者娓娓道來他和書的故事。言談之間,濃濃的書卷之氣流露而出。
“我這一生先是‘讀書’,然后在劇團‘唱書’,還在學校‘教書’,最后去了巴中市圖書館‘管書’。”彭德泉回憶,2005年,臨近退休前幾年,我去拜見了自己的恩師,中國著名圖書館學家、目錄學家張德芳,當時,老師身患重病,卻拉著我的手不厭其煩地說,“你不要整天泡在圖書館,趕緊出來搶救古籍,書都要爛完了,再晚就來不及了。”
張德芳的著急,正是源于古籍瀕危的現狀。四川盆地溫熱潮濕,加上保存管理不當等人為因素,相當多的館藏古籍文獻出現不同程度的霉變、蟲蛀、鼠嚙、斷裂、殘損等破損情況。
“我一聽也著急起來。”彭德泉說,等我走訪調研后發現,實際情況比料想中還要糟糕,大量古籍正在走向不可逆轉的損毀。
他說,“一開始,愛人和孩子是不理解我的,不明白我臨近退休為何還要折騰,但我堅持辦理了離崗待退手續,四處找人商量,應該怎么搶救古籍文獻。”
回憶起修書的最初,盡管時隔十多年,年逾古稀的彭德泉也不禁哽咽,“先人歷經戰亂災荒,艱難地讓這些古籍流傳至今,在和平年代,珍貴的古籍怎么能從我們手里消失?不修好,怎么對得起先人和后人?”
于是,在張德芳的感召下,彭德泉聯合幾位有共同志向的友人——時任廣漢市圖書館館長秦一、省圖書館退休的古籍修復專家劉英等,一起開始了古籍修復之路。
“古籍修復是個專業活,也是個苦差事,一開始,我們通過開辦古籍修復培訓班招募人才。”彭德泉講述,我們以首批培訓班的5名學員成為原始班底,在廣漢圖書館開始古籍修復工作。
初建的古籍修復隊伍沒有經費,也沒有專業的工具,為了壓書,大家出去撿石板、磚塊,甚至把舊家具鋸了當作壓平機;古籍多霉菌、螨蟲、飛蟲,長期做著古籍工作,嗆得人不斷咳嗽,時常出現過敏癥狀。
“最緊張時,連每個月300元的工資都發不出。”說到此處,彭德泉的臉上滿是愧疚,“我年紀大些,為了情懷能夠不求回報,但對年輕人來說,要生活,要吃飯。”
“讓我沒想到的是,在這樣艱難的情形下,大家卻沒有離開,他們跟我說,‘彭老師,跟著你干這個,誰不是憑著一腔熱愛,本來也不是圖錢,我們相信,以后一定會越來越好’。”時隔多年,彭德泉仍對這一番話記憶猶新。
就是這一股勁支撐著他們,2008年,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在廣漢正式注冊成立;2012年,成都博物院為他們免費提供了辦公場所,在成都成立了分中心,主要人員搬遷到成都;2016年,再搬遷到洛帶古鎮,他們不僅在這里建立了古籍文獻修復博物館,還壯大了修復團隊,走向快速發展階段。
2019年揭牌的洛帶·藝匠古籍文獻修復博物館是國內第一家以展示紙質文獻修復技藝為主題的博物館。開辦這個博物館也是彭德泉一生的心愿。
博物館不僅科普了古籍修復的各類知識,更是展示出古籍修復大師、高浮雕傳拓大師終其一生艱苦求索的修復技術、工具及學術成果。
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是全國“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所”中唯一的民營機構。“這么多年來,我們得到了國內多位專家、大師的無私傳授,他們作為中心的顧問來授課、指導、收徒,從來沒收過一分錢。”彭德泉列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古籍修復技藝代表性傳承人杜偉生在我們這收了11個徒弟,毫無保留地把畢生技藝教授給他們。
“和修復古籍同等緊急的,是修復技藝的傳承,這也是開辦這個博物館的初衷。”彭德泉說,修復古籍需要20多道傳統工序,如配紙、染紙、配線、配制糨糊、裱書衣、書簽等,掌握這些技藝的專家大多年歲已高,對古籍修復技藝同樣需要搶救性傳承。
博物館揭牌這天,杜偉生前來參加,他贊道,“你們干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對保存、珍視、傳承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做出了重要貢獻。”
如今,在彭德泉兩次出現腦梗入院后,兒子彭克考慮到父親的身體狀況,辭去了公職,從父親手中接過古籍修復“接力棒”。
“但我還要再貪心一點。”彭德泉說,我還有兩個心愿,一是希望發展到60人以上的修復隊伍,搶救更多的古籍文獻;二是希望能把員工工資再提高一些,“這樣,我就能安心退休了”。
“70后”母親
既是修補古籍也是修復心靈
人物檔案
李婷玉: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培訓部部長,從金融行業“轉戰”古籍修復行業,與古籍相互“治愈”,目前致力于開發古籍研學課程,在中小學校推廣古籍傳統文化。
3月中旬,一場研討會上,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培訓部部長李婷玉向大家推介了一整套的研學課程。
“傳統文化教育,傳統紙張制作、活字印刷體驗、動手修復古籍……我們通過各類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淺出地普及古籍相關的傳統文化,讓古籍走出博物館、走進校園。”活動現場,李婷玉的一番介紹引起了不少參會學校的興趣。
40出頭的李婷玉是西部文獻修復中心的“跨界”典型。
“過去我從事金融行業,沒想到‘半路出家’加入到古籍修復隊伍。”她感慨,這幾年來,我和古籍是相互“治愈”。
李婷玉從小熱愛傳統文化,在自己小孩剛上小學時,就著手為孩子設計各類傳統文化課程,“或許是此時‘望子成龍’心切,但凡孩子學習中出現差錯,我就十分焦躁,母子關系一度很是緊張。”
后來經人介紹,李婷玉參加了西部文獻修復中心的古籍修復師培訓班,還經常帶著孩子一起聽課。
“一下子感覺找到了心靈的契合。”李婷玉說,結業后,我通過現任西部文獻修復中心主任彭克了解到,他們正著手開發面向中小學的古籍修復培訓課程,傳播傳統文化,讓古籍文獻“活起來”。
“或許我可以幫上些忙。”李婷玉想著。在著手設計了一些針對小朋友的課程教案后,彭克向她拋出“橄欖枝”,“愿不愿意正式加入西部文獻修復中心?”
李婷玉動心了,但她仍有疑慮,“我不是科班出身,金融行業節奏快,容易讓人浮躁,古籍修復截然不同,講究一個慢字,要沉下心來,耐得住寂寞。”
“我們不看員工出身背景,更重要的是耐心、細心和責任心。”彭克說。
2019年,李婷玉正式加入西部文獻修復中心,一邊學習實操技術,一邊設計課程、對接學校。她在金融行業鍛煉的敏銳市場嗅覺,派上了用場,很快便打開了局面,聯系上幾家學校開展古籍修復研學課程。
這期間,李婷玉與兒子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親密,“我們嘗試共同修復一張古籍書頁,在錄制古籍宣傳教育視頻時,也常讓兒子來當小模特。”
“這是修書也是‘修心’,過去,我的浮躁和焦慮影響了身邊人,現在靜下心來,體會到的是理想信念和堅守傳承的力量。”李婷玉坦言。
兩年多來,西部文獻修復中心的研學課程已開展兩百多節。李婷玉也成為了中心的骨干力量,擔任培訓部部長,帶領著她的團隊,以另一種方式,讓古籍煥發新生。
李婷玉的成長背后,正折射出修復中心的發展新思路——吸納越來越多的“跨界”人才,推廣古籍、活化古籍。
“95后”新生力量
古籍修復師是她心中的“月亮”
人物檔案
黎彥君:1996年生于巴中,扎根西部文獻修復中心3年,成為這里的技術骨干,立志要將古籍修復作為自己的終生職業規劃。
“95”后的黎彥君是西部文獻修復中心青年后生的代表。
圓框眼鏡、齊肩短發,說起古籍修復便滔滔不絕,眼中散發著光芒……黎彥君大學畢業后來到修復中心三年有余,已從最初的“小白”蛻變為技術骨干。
拿到破損的文獻,每一頁拍照編號,把書籍裝訂拆開,用噴壺清洗書頁,在背面鋪上一張宣紙,用調制的糨糊把每一個蟲洞補上……修書如同繡花,日復一日,黎彥君與同事們在操作臺前一坐就是一整天。
“這不是一項多么有趣的工作,但每修好一冊書、一幅字畫,真的很有成就感。”在黎彥君看來,這種修繕的成就感就是支撐她走下去的動力。
“緊張得手一直在抖!”回憶起第一次修復古籍時的情景,她記憶猶新,經過歲月的沉淀,這些古籍雖然破舊,但那一頁頁輕薄、在燈光照射下透著光亮的紙張都好似有生命力,無聲訴說著曠日持久的故事。
緊張的背后,是修復師對古籍的珍視和敬畏之情。
古籍修復全靠一雙巧手,錘子、尺子、鑷子、毛筆、棕刷、噴壺等工具讓人眼花繚亂,修復中心聘用的每一個員工,都要經過6到9個月的封閉式培訓,通過考試后才能正式入職。
黎彥君介紹,學徒生涯是“很枯燥難熬的”,訓練剪紙、裁紙等基本功,學習辨別紙張顏色、厚薄等,是古籍修復中最基礎也是最煩瑣的部分,她比劃著,“學員必須要練成在沒有任何參考物情況下,用剪刀剪出一條直線,但我是個‘左撇子’,左手不好發揮,我就只能反復練習,那時是冬天,一天下來,手指凍得僵硬沒有知覺。”
正式入職后,也有難熬的時刻。“遇到高難度的書冊,有太多的破損和病害,要么是根本不知從何入手,要么是剛剛費盡心思解決了這個修復難題,立馬遇上下一個。”黎彥君說,“很挫敗,心態就崩了!”
這時,修復中心的同事往往會相互鼓勵和打氣。做古籍修復,工資待遇并不高,黎彥君卻將此作為終生職業,她說道,如果大部分人都去追求“六便士”,那么總要有人追求“月亮”,而古籍修復師這個職業就是她心中的“月亮”。
如今,伴隨著更多新生力量的加入,黎彥君已不再是西部文獻修復中心最小的修復師,不少剛畢業的年輕人也加入到古籍修復中來。
這群生長在互聯網時代的年輕人,為這項“清冷”的工作帶來了溫度。
彭克時常鼓勵他們,“在新時代,如何利用新材料、新技術進行古籍文獻保護的創新,如何利用微博、抖音、B站等新媒體平臺,讓古籍會說話,讓更多人了解古籍,是你們要探索的課題。”
盡管充滿挑戰,但在年輕一代修復師神采飛揚的眼神中,青春洋溢的面龐上流露出滿滿的自信。(吳亞飛)